


作者:劉余莉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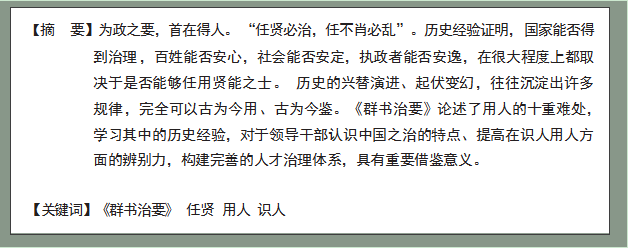
《群書治要》是我國古代治政書籍的選輯, 由唐太宗于貞觀初年下令編輯。據(jù)《唐會要》卷三六《修撰》記載:“貞觀五年九月二十七日, 秘書監(jiān)魏徵撰《群書治要》上之”,夾注中說:“太宗欲覽前王得失,爰自六經(jīng),訖于諸子,上始五帝下盡晉年,徵與虞世南、褚亮、蕭德言等始成凡五十卷,上之。諸王各賜一本”。魏徵在序文中稱之“用之當(dāng)今,足以鑒覽前古;傳之來葉,可以貽厥孫謀”。唐太宗讀《群書治要》后,在《答魏徵上〈群書治要〉手詔》中感慨道:“覽所撰書,博而且要,見所未見,聞所未聞,使朕致治稽古,臨事不惑。其為勞也,不亦大哉!”他認(rèn)為此書廣博而切要,特令繕寫十余部,分賜太子及諸侯王以作從政龜鑒。
由于當(dāng)時(shí)雕版印刷尚未發(fā)達(dá),《群書治要》一書至宋朝初年就已失傳。所幸《群書治要》被“遣唐使”帶到日本,被日本歷代天皇及皇子、大臣奉為圭臬,因此在流傳的過程中也幾經(jīng)抄寫、刊刻、印刷。目前可知的日傳《群書治要》就有九條家本、金澤文庫本、元和本、天明本、天明刊寬政修本、弘化本、昭和本等不同版本,其中1945年發(fā)現(xiàn)的九條家本(殘卷)在1952年被定為日本國寶,藏于國立東京博物館。2018年6月21日,日本前首相細(xì)川護(hù)熙,代表日本永青文庫向中國國家圖書館捐贈36種4175冊珍貴漢籍,其中就包括《群書治要》。這一治世經(jīng)典對日本的影響由此可見一斑。日本學(xué)者林信敬在《群書治要》天明本的校正序中指出:日本承和、貞觀年間(約公元834—876年),社會呈現(xiàn)出安定繁榮的盛世局面,應(yīng)該就是因?yàn)橹v學(xué)研讀這部書所成就。島田翰在《漢籍善本考》中稱嘆金澤本《群書治要》時(shí)說:“筆精墨妙,光耀日月,數(shù)百歲下,俾人凜然生敬也。顧亦繼今而后之君子,茍有拜秘府之藏也讀斯書也,則必有思所以斯書之存于今者,感極而泣若予者矣!而唐士之人讀斯書,則其尊崇威敬之心,其有不油然而生者耶?”
誠如斯言,20世紀(jì)90年代,中國原駐日大使符浩先生從日本皇室獲贈一套天明版《群書治要》,由唐史研究專家呂效祖先生等對其點(diǎn)校考譯,著《〈群書治要〉考譯》一書。2001年2月25日,時(shí)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、中央書記處書記習(xí)仲勛同志為之親筆題詞:“古鏡今鑒”。習(xí)近平總書記在2015年發(fā)表新年賀詞時(shí),在辦公室書架的顯著位置擺放的正是大部頭的《群書治要》。而且因?yàn)椤度簳我氛浀脑行┰谖宕蟊阋咽鳎?nbsp;唯有在《群書治要》保留了其精華內(nèi)容,如《尸子》《申子》《桓子新論》《崔寔政論》《昌言》《典論》《劉廙政論》《蔣子萬機(jī)論》《政要論》《體論》《時(shí)務(wù)論》《典語》《傅子》《袁子正書》等,這更使得《群書治要》具有獨(dú)特的文獻(xiàn)價(jià)值。由此也可得知,習(xí)總書記用典中凡是引自以上典籍的名言皆出于《群書治要》。這說明,《群書治要》不僅是唐太宗創(chuàng)建“貞觀之治”的理論基礎(chǔ),也可為中國共產(chǎn)黨建設(shè)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所借鑒,成為實(shí)現(xiàn)“中國之治”的一個(gè)思想源泉。
《群書治要·孔子家語》中記載,孔子在為曾子講解治理天下的最高境界時(shí),提到“三至”:“至禮不讓而天下治;至賞不費(fèi)而天下之士悅;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。”至高的禮不需要講謙讓,天下就能夠得到治理;最高的獎(jiǎng)賞不需要耗費(fèi)資財(cái),天下的士人都喜悅;最高境界的音樂不需要發(fā)出聲音,就能使天下的百姓感到滿足而和睦相處。如果明智的君主能夠認(rèn)真實(shí)行“三至”,結(jié)果就是天下的君主都知曉他的名聲,天下的士人都愿意做他的臣子,天下的人民都可為他所用。
曾子聽后,請求孔子詳加解釋其深意。孔子說:古代明智的君主熟知天下賢德之士的名字。不僅如此,還要調(diào)查他們是否名副其實(shí)。如果他們的確名副其實(shí),就給予他們一定的名位。這就是最高的禮不需要謙讓,天下便能夠得到治理。用天下的俸祿,使這些賢德之士富裕,這就是最高的獎(jiǎng)賞不需要耗費(fèi)太多資財(cái),天下的士人都喜悅。只要君主封賞的都是有德行的賢良之士,天下之人都會稱贊領(lǐng)導(dǎo)者英明。如果領(lǐng)導(dǎo)者能做到這些,天下贊嘆的聲音自然就興起來了,這就是至高的音樂不需奏出聲音,天下的人民都能和睦相處。
要達(dá)到這種理想的治理境界的關(guān)鍵就是要領(lǐng)導(dǎo)者賢明,能夠知人善任。因?yàn)槿绻t德之士在位,他們的言傳身教會使人民自然受到良好教化,彼此和睦相處,人民也會心悅誠服為國君所用。
治理的最高境界說起來很容易,但實(shí)行起來達(dá)到效果卻很難。因?yàn)樵趯?shí)踐中,君主任用賢德之士存在著各種難處。《群書治要·申鑒》把這些困難總結(jié)了十條。這十條難處可以歸納為三個(gè)方面。
“一曰不知。”即沒有識人之明, 因而不能辨別誰是真正賢明的人。 老子曰:自知者明,知人者智。孔子曰:不患人之不己知,患不知人也。這些都說明知人并非易事,要有相當(dāng)?shù)谋鎰e能力。
“二曰不求。”即不知道用心去求取人才。《群書治要·傅子》說:“夫圣人者,不世而出者也。賢能之士,何世無之。”圣人確實(shí)不是世世代代都有的。古人說,“五百年而有王者興”,五百年才出現(xiàn)一位圣王。但是賢德之士,哪一個(gè)時(shí)代沒有呢?既然如此,為什么領(lǐng)導(dǎo)者卻得不到人才?
《傅子》中對此論述道:虞舜、文王、武王等圣人,想要實(shí)行王道,賢臣就會出現(xiàn)來輔佐他們;齊桓公想要稱霸天下,管仲這樣的臣子就出現(xiàn)了;秦孝公想要富國強(qiáng)兵,商鞅這樣的法士也就來輔助他了。“欲王則王佐至,欲霸則霸臣出,欲富國強(qiáng)兵,則富國強(qiáng)兵之人往。求無不得,唱無不和,是以天下之不乏賢也,顧求與不求耳,何憂天下之無人乎?”至圣的明王一旦倡導(dǎo),天下的賢人自然會應(yīng)和。天下并不缺乏賢才,只看求與不求罷了,怎么會憂愁天下沒有人才?
《群書治要·說苑》記載,齊宣王請淳于髡談?wù)撘幌滦跤惺裁磹酆谩4居邝照f:“古代君王所喜歡的有四種,而大王只喜歡其中的三種。”齊宣王問其故。淳于髡說:“古代的君王喜歡駿馬,大王也喜歡駿馬;古代的君王喜歡美味,大王也喜歡美味;古代的君王喜歡美色,大王也喜歡美色。但是,古代的君王喜歡賢士,唯獨(dú)大王您不喜歡賢士。”齊宣王聽后說:“國家沒有賢士,如果有賢士,我自然喜歡他們。”淳于髡說:“古代有驊騮、騏驥這樣的駿馬,現(xiàn)在沒有這樣的駿馬了,但大王會從眾多的馬中去選取,可見大王您是真的喜好駿馬;古代有豹胎、象胎這樣的美味,現(xiàn)在沒有這樣的美味了,但是大王也會從眾多的美味中去選取,可見大王也是真的喜好美味;古代有毛嬙、西施這樣的美女,現(xiàn)在沒有了毛嬙、西施,但是大王也會從眾多的美女之中去選取,可見大王也是真喜歡美色。如果大王一定要等待堯舜禹湯時(shí)代那樣的賢士出現(xiàn)才喜歡他們,那么堯舜禹湯時(shí)代那樣的賢士也就不喜歡大王您了。”齊宣王聽了之后默默無語。這則故事說明,天下其實(shí)并不缺少賢士。世間德才兼?zhèn)涞娜撕芏啵皇蔷酰I(lǐng)導(dǎo)者)沒有用心去求取罷了。
求取賢才,關(guān)鍵在于領(lǐng)導(dǎo)者對賢才要有恭敬、禮遇、真誠的態(tài)度。所以,禮敬賢才、重視賢才與否,是評價(jià)一個(gè)領(lǐng)導(dǎo)者是否賢明的重要標(biāo)志,更是一個(gè)領(lǐng)導(dǎo)者能否建功立業(yè)的根本保證。
《孔子家語》記載,魯哀公向孔子請教當(dāng)時(shí)的君主誰最賢明。孔子說:“我沒有遇到過賢明的君主,如果非要說有一位賢明君主的話,那就是衛(wèi)靈公吧。”哀公問其原因。孔子說:“衛(wèi)靈公的弟弟公子渠牟的智慧、信義可以治理千乘兵車的中等國家,衛(wèi)靈公很喜愛并且非常重用他。衛(wèi)國的士人王林國,如果發(fā)現(xiàn)賢德之人,就一定會舉薦,如果看到賢德之人被退黜,就把自己的俸祿分給他,所以衛(wèi)國沒有被埋沒的讀書人。衛(wèi)靈公知道了這件事,便對王林國非常尊敬。衛(wèi)國有一位士大夫慶足,每逢多事之秋,他一定會出來輔佐君主國家;當(dāng)國泰民安時(shí),他便從官位上退下來,把位子讓給那些賢德的人。衛(wèi)靈公對他非常尊敬,奉為上賓。衛(wèi)國還有一位大夫史鰍,開始與衛(wèi)靈公政見不和,便想離開衛(wèi)國。后來衛(wèi)靈公知道自己錯(cuò)了,在郊外住了三日,反省自己,琴瑟不奏,一定要等史鰍回國之后,靈公方肯回朝。所以,我認(rèn)為衛(wèi)靈公是一位賢明的君主。”可見,孔子認(rèn)為真正賢明的君主,一定是知人善任之人,非常重視求取賢德之士。而要求取賢德之士,君主必須有禮賢下士的態(tài)度。
《群書治要·尸子》中說:“下士者得賢,下敵者得友,下眾者得譽(yù)。故度于往古,觀于先王,非求賢務(wù)士,而能立功于天下,成名于后世者,未之嘗有也。夫求士不遵其道,而能致士者,未之嘗見也。”禮賢下士的人能夠得到賢才,能夠?qū)橙硕Y敬的人可以化敵為友,能夠?qū)Ρ娙硕Y敬的人可以獲得眾人的稱譽(yù)。縱觀整個(gè)歷史發(fā)展和古代圣王的治國經(jīng)驗(yàn),如果不依靠賢才,沒有哪個(gè)先王可以立功于天下、成名于后世。如果君主沒有按照正道來求取賢才,賢才也招致不來。這說明領(lǐng)導(dǎo)者真誠、禮敬的態(tài)度非常重要。領(lǐng)導(dǎo)者對賢德之士有真誠恭敬的態(tài)度,才能得到賢能之士的真誠幫助,成就事業(yè)。
“三曰不任。”即不能任用賢德之士。《群書治要·中論》記載:即使是末代的亡國之君,其朝廷中也不是沒有可以使天下大治的臣子,其府庫中也不是沒有圣賢的典籍,但他們最終免不了滅亡,原因就在于“其賢不用,其法不行也”。有賢德的人,但是不被君主重用;有圣賢的典籍及治國的方法、策略,但是沒有被君主推行。這就是“千里馬常有,而伯樂不常有”。
《孔子家語》中記載,子路請教孔子:“賢明的君主治國首先應(yīng)該重視什么?”孔子說:“尊敬賢德的人,輕賤不賢德的人。”子路又問:“可是我聽說晉國的中行氏也尊敬賢德的人,輕賤不賢德的人,為什么他還是滅亡了?”孔子說:“中行氏尊敬賢德的人,卻不能任用他們;輕賤不賢德的人,卻不能夠罷免他們。賢德的人知道中行氏不重用自己,就有怨恨之心;不賢德的人知道他輕視自己,就對他有仇恨之心。怨、仇這兩種情緒并存于國家,而鄰國的敵兵又在郊外作戰(zhàn),中行氏想不滅亡,怎么可能呢?”如果像中行氏這樣,有了賢德的人卻不能重用,有不肖之人卻不能罷免,這樣就很難治理好國家,事業(yè)也很難興盛。
《群書治要·六韜》列舉了七種賢者不能夠被國君重用的具體原因:第一,“主弱親強(qiáng),賢者不用”。君主弱小,他的親屬勢力強(qiáng)大,權(quán)力無法集中在君主的手中,即使出現(xiàn)了賢德的人,也不能被君主重用。第二,“主不明,正者少,邪者眾,賢者不用”。君主不夠明智,而身邊正直的人少,邪曲不正的人多,賢德的人也不會被重用。第三,“賊臣在外,奸臣在內(nèi),賢者不用”。賊臣在外誹謗,奸臣在內(nèi)進(jìn)獻(xiàn)讒言,賢德的人也不會被重用。第四,“法政阿宗族,賢者不用”。法律政策都是偏向于自己的親戚,導(dǎo)致任人唯親,而不是任人唯賢,這樣賢者就得不到重用。第五,“以欺為忠,賢者不用”。把欺騙自己的人當(dāng)成是忠臣,賢者就不會被重用。第六,“忠諫者死,賢者不用”。忠臣發(fā)現(xiàn)國君有錯(cuò)誤,不惜犯顏直諫,指正其過錯(cuò)。但是君主喜歡巴結(jié)諂媚、阿諛奉承的人,厭惡直言不諱的人,不僅不獎(jiǎng)賞賢臣,反而會置賢臣于危險(xiǎn)的境地,這樣賢者也得不到重用。第七,“貨財(cái)上流,賢者不用”。財(cái)貨都流到上層,也就是君主貪財(cái)好利,而賢德的人最大的特點(diǎn)就是沒有自私自利、貪財(cái)好利的心。君主有這種喜好,賢德的人當(dāng)然不會得到重用。古人把這些賢德之人不被重用的情況都列舉出來,警示后代的領(lǐng)導(dǎo)者要引以為鑒。
“四曰不終。”即雖然任用了賢德之人,但是不能善始善終。《群書治要·典語》中將君主和臣子之間的關(guān)系作了一個(gè)形象的比喻:“夫君稱元首,臣云股肱,明大臣與人主一體者也。”古代的人把君主稱為頭腦,把臣子稱為大腿和胳膊,也就是四肢,表明大臣和君主原本是一體的關(guān)系,就像一個(gè)身體一樣,誰也離不開誰,互相配合,互相信任。堯帝能夠明了地辨別德才兼?zhèn)涞娜耍⑶易尩虏偶鎮(zhèn)涞娜藫?dān)任官職,這樣就如同強(qiáng)健了四肢,也就能輔助身體,對自己的幫助怎么會小呢?如果一個(gè)人不符合選拔的標(biāo)準(zhǔn),就不要白白地授予他官位;如果真正得到了德才兼?zhèn)涞娜瞬牛鸵斡脹]有懷疑。這樣,君主任用臣子就像身體信任他的手一樣;反過來臣子侍奉君主,也就像手觸摸他的身體一樣。他們共享安樂,共同患難,是一體的關(guān)系,誰也離不開誰,怎么能夠互相懷疑呢?這說明,君主和大臣的關(guān)系就像頭腦和四肢的關(guān)系一樣,應(yīng)該是互相信任,而沒有任何疑慮之心,只有這樣任用賢才才能善始善終。
“五曰以小怨棄大德。六曰以小過黜大功。七曰以小短掩大美。”這幾條都是指在用人過程中求全責(zé)備。
《群書治要·袁子正書》中說:“故凡用人者,不求備于一人。”齊桓公和寧戚的故事講的就是這個(gè)道理。寧戚想去侍奉桓公,但是他窮困潦倒,沒有辦法舉薦自己。于是,他就為那些走商的人駕車,終于到了齊國,晚上住在城門之外。這時(shí),齊桓公到郊外去迎接客人,晚上開了城門,讓趕車的人都回避。寧戚正好在車下喂牛,看到桓公,趕緊敲響牛角, 唱起了凄厲的商歌。桓公聽到歌聲后說:“這個(gè)唱歌的人可不是平凡之人。”由此可見,桓公也很了不起,他聽一個(gè)人的歌聲,就知道這個(gè)人不平凡。
于是,齊桓公就命令把寧戚載進(jìn)城去。齊桓公返回國內(nèi),寧戚來求見,勸說桓公要統(tǒng)一整個(gè)國家。第二天,寧戚又來求見,勸說他要稱霸天下。齊桓公聽了他的進(jìn)諫,非常高興,就想任命他做官,委以重任。但是在這個(gè)時(shí)候,群臣有不同意見。有人說,此人是魏國人,魏國離齊國不遠(yuǎn),不如派人去打聽一下,如果他確是賢才,又有德行,再任用也不遲。桓公說:“你講得不對!如果去打聽他,恐怕他會有小的過惡,因?yàn)樗行〉倪^惡,就忘記了他大的好處,這是君主所以失去天下賢士的原因。而且人才本來就是難以用尺度去衡量的,并非十全十美,我們只要用他的長處就可以了。”桓公沒有派人去打聽寧戚的為人,而是對他委以重任,封他為卿。正因?yàn)辇R桓公這個(gè)舉動(dòng)得當(dāng),所以得到了賢士,能夠稱霸天下。
由此可見,大多數(shù)人都不是圣賢人,免不了有一些小的過失、缺點(diǎn)、不足,如果希望人沒有任何瑕疵,幾乎是不可能的。所以,任人不能求全責(zé)備。
《群書治要·文子》中說:“今人君之論臣也,不計(jì)其大功,總其細(xì)行,而求其不善,即失賢之道也。”現(xiàn)在的君主評論臣子時(shí),不在意他大的功勞和貢獻(xiàn),而在他細(xì)小的行為上做文章,挑剔他小的不善、小的錯(cuò)誤,這是失去賢士的原因。“故人有厚德,無問其小節(jié);人有大譽(yù),無疵其小故。”所以,一個(gè)人有很高尚的德行,就不要在他細(xì)小的行為上做文章;一個(gè)人有很大的聲譽(yù),就不要在小的不足上去挑剔。這說明,人無完人,如果想求取十全十美、一 點(diǎn)錯(cuò)誤都不犯的人,的確很難。
《文子》中說:“自古及今,未有能全其行者也。故君子不責(zé)備于一人。夫夏后氏之璜,不能無瑕;明月之珠,不能無穢。然天下寶之者,不以小惡妨大美也。今志人之所短,而忘人之所長,而欲求賢于天下,即難矣。”從古至今,從歷史上看,沒有十全十美、德行無可挑剔的人,所以君子不求全責(zé)備于任何一個(gè)人。后面還作了兩個(gè)很好的比喻:夏禹佩戴的璧玉,也不是沒有瑕疵的;夜明珠,也不是沒有污點(diǎn)的。但是天下人仍然認(rèn)為它們是寶貴的東西,不以小小的瑕疵來妨礙它們的大美。如今只記著別人的短處,而忘記了他的長處,還想在天下求得賢才,這是難上加難。
由此可見,即使是很珍貴的璧玉、夜明珠,都不是沒有瑕疵的。如果君主對人求全責(zé)備、過于苛刻,還想求得賢才,也是不可能的。古人講:“任人之工,不強(qiáng)其拙。”這是任人的大綱。可見,任人不能求全責(zé)備,否則也會失去賢才。
“八曰以干訐傷忠正。”《群書治要·劉廙政論》中說:“自古人君,莫不愿得忠賢而用之也。既得之,莫不訪之于眾人也。忠于君者,豈能必利于人?茍無利于人,又何能保譽(yù)于人哉?”自古以來,做君主的沒有不想得到忠賢之士而任用的。但是得到這些忠賢之士后,卻又不免去向眾人調(diào)查。忠于君主的人哪里能夠事事都有利于他人?如果有一件事得罪了人,沒有為人帶來利益,怎么能夠讓眾人都稱贊,在眾人中都得到好的名聲呢?
如果君主自己不賢明,就不知道什么樣的人是忠賢之士。即便忠賢之士已經(jīng)到他身邊來輔佐,君主也會懷著一種猜疑之心,向眾人再去調(diào)查。而眾人又不一定都是賢德忠正之人。那么,奸邪之人就會對賢德之士有一些偏頗的言語和評論。如果君主聽之任之,就會對忠賢之士產(chǎn)生懷疑,從而不予重用。
《群書治要·體論》中記載:“使賢者為之,與不肖者議之;使智者慮之,與愚者斷之;使修士履之,與邪人疑之,此又人主之所患也。”任命了賢德之人做事,又讓不賢德之人來議論他;讓有智慧的人來謀劃,卻又讓愚鈍的人來決斷;讓有修為的人去履行某一件事,卻讓奸邪之人去懷疑他,這些也是君主經(jīng)常犯的錯(cuò)誤。正是因?yàn)檫@些君主對于賢德之人不能做到用而不疑,經(jīng)常產(chǎn)生猜慮之心,結(jié)果使得賢才的才華不能得到充分施展,這也是失去賢才的一個(gè)重要原因。
“九曰以邪說亂正度”,即以邪說擾亂正規(guī)的法度。這個(gè)法度,是指治國的常理常法,也就是“五倫”“五常”“四維”“八德”,等等。
《孔子家語》記載,孔子去做魯國的司寇。上任才幾天,就把少正卯殺了。因?yàn)樯僬詡味q,能言善道,別人都辯不過他,但是他所講的都是有違于大道的,會擾亂民心,使人心迷惑。對于這樣“以邪說亂正度”的人,只好把他殺掉。
“十曰以讒嫉廢賢能。”因讒言嫉妒而廢棄了賢能之士。《戰(zhàn)國策》中“三人成虎”的故事,說的就是這個(gè)道理。
魏國大臣龐蔥很受魏王的器重。魏王派龐蔥陪同世子去趙國做人質(zhì)。龐蔥知道國君很容易受左右之人的影響,聽信讒言。所以,臨行之前,他向魏王講述了一則寓言。他說:“大王,如果有人對您講,大街上有一只老虎,您會相信嗎?”魏王想都沒想,說:“寡人當(dāng)然不信,老虎招搖過市,這種事情怎么可能發(fā)生?”龐蔥接著問道:“如果又有一個(gè)人從街市上回來,告訴大王街上有一只老虎,這回大王信嗎?”魏王猶豫了一下,說:“這就很難說了,要考慮一下。”龐蔥繼續(xù)問:“如果第三個(gè)人也這樣說,大王會信嗎?”魏王肯定地點(diǎn)了一下頭,說:“如果三個(gè)人都這樣講,那肯定是真的了。”龐蔥說:“街上怎么可能有老虎?街上沒有老虎是事實(shí),那些說有老虎的人只是在互相傳謠而已。可是大王您為什么會相信?就是因?yàn)檎f的人太多了,所以大王才相信。而現(xiàn)在我和世子要到趙國做人質(zhì),趙國遠(yuǎn)離魏國,比從這到大街的距離不知道遠(yuǎn)多少倍。而這時(shí)候如果進(jìn)讒言、誹謗我們的人又不止三個(gè),大王可能就會懷疑我們。希望大王您能夠明察。”魏王聽了之后說:“我知道該怎么辦。”
龐蔥走后,毀謗的聲音很快就傳到了魏王那里。結(jié)果當(dāng)世子結(jié)束了人質(zhì)的生活,回到魏國時(shí),龐蔥就再也見不到魏王了。這說明,魏王已經(jīng)不再信任他,也不想任用他了。由此可見,讒言的力量是多么可怕。即使魏王已經(jīng)提前受到提醒,做過預(yù)防,但是仍然敵不過讒言的泛濫。
古人說:“謠言止于智者”。特別是領(lǐng)導(dǎo)者要知道“來說是非者,便是是非人”。一個(gè)真正有德行的人,真正希望團(tuán)隊(duì)團(tuán)結(jié)和諧的人,是絕對不會故意制造矛盾,影響人際和諧的。
聽信讒言的原因在于“讒不自來,因疑而來;間不自入,乘隙而入。”所以,古圣先賢教導(dǎo)君主“反求諸己”,要檢討自己是否疑心太重,對身邊的人有成見、有嫌隙,才使讒言趁機(jī)而入。
而進(jìn)讒言者一般都是出于嫉妒之心。嫉妒心讓人心理失衡,還容易導(dǎo)致怨恨,甚至因此還做出一些誹謗、傷害他人的行為。
在重用賢才方面,要排除這十種難處,才能夠使賢人、圣人受到重用。孔子是圣人,在世時(shí)周游列國,希望自己的仁愛學(xué)說能夠?yàn)橐晃婚_明國君所采用,把國家治理好,為天下人做出良好的示范,讓天下人都來學(xué)習(xí),卻也遭遇了重重困難。
當(dāng)孔子到達(dá)楚國的時(shí)候,楚昭王本來都想重用孔子了,為了表示自己對孔子的敬重,還想把有居民的方圓七百里的土地封給孔子。但是,令尹子西進(jìn)讒言說:“大王您看,在您出使諸國的使者之中,有像孔子的弟子子貢這樣的人才嗎?”楚昭王一想,說:“沒有。”子西又說:“大王的相國之中,有誰的德行能和顏回相比嗎?”楚昭王說:“沒有。”子西說:“大王的將帥之中,有像子路這樣的人物嗎?”楚昭王又說:“沒有。”子西說:“大王的各部長官,有像宰予這樣的人才嗎?”楚昭王仍然說:“沒有。”令尹子西說:“楚國的祖先在周受封時(shí),封號是子、男的爵位,封地僅有方圓五十里。現(xiàn)在孔子修習(xí)三王五帝治理天下之道,彰明周公、召公的德業(yè),大王如果任用他,那么楚國還能世世代代保住泱泱數(shù)千里的土地嗎?周文王在豐地,周武王在鎬地,領(lǐng)地才不過方圓百里,原本只是小國的國君,最后都能夠稱王天下。而現(xiàn)在如果孔丘占有方圓七百里的土地,又有賢能弟子的輔佐,這恐怕不是楚國的福分。”楚昭王聽了之后,認(rèn)為他說得很有道理,于是就放棄了給孔子封地、重用孔子的想法。這完全是因?yàn)榫鳑]有知人之明, 以小人之心度圣人之腹。
圣人周游列國,并不是想升官發(fā)財(cái),而是希望遇到一位明君,能夠把自己仁愛學(xué)說推廣于天下,讓百姓過上幸福生活,社會和諧,天下太平。但是這些國君、臣子往往以小人狹隘的私心揣度圣人的心量,結(jié)果導(dǎo)致圣人在世時(shí)也不能被重用。所以,古人說不世之臣要遇到不世之君,才能建立不世之功。即卓越的臣子要遇到英明的君主,才能夠建立不朽的功勛,否則即使如圣人孔子也難免被埋沒。
“十難不除,則賢臣不用。賢臣不用,則國非其國也。”如果以上列舉的十難不排除,賢臣就不能被起用;賢臣不被起用,國家就不成其為國家了。如果君主不能任賢遠(yuǎn)佞,或者任人出于個(gè)人的喜愛,任人唯親,都必然招致國家的敗亡。
《群書治要·昌言》中說:如果君主任用的人,不是自己的親屬就是自己寵幸的人,沒有任人唯賢而是任人唯親,任人出于自己的喜好;所愛的不是美女,就是諂媚巴結(jié)的人;以和自己的觀點(diǎn)相同與否作為評判好人壞人的標(biāo)準(zhǔn),根據(jù)自己的喜怒來行賞罰;喜歡美女而忽視朝政,不理國家大事,百姓被冤枉、殘害。在這種情況下,雖然對待各方祭祀非常恭敬,毫不違背四時(shí)之禮;審判案件都是嚴(yán)格地在冬日行刑,按著四時(shí)的規(guī)律處理國家大事;用于占卜的蓍草和龜甲,堆積于廟門之中;用以祭祀的純色牲畜,都成群成對地系在豎石之上;占星的人坐在占星臺上不下來,祝史跪在祭壇旁不離去。縱使做到了所有這些,也無益于挽救敗亡。
這段話意義深刻,告訴君主治國的關(guān)鍵在于能夠“任人唯賢”。賢德之人能夠教導(dǎo)百姓孝悌忠信、禮義廉恥的道理,真正把人心轉(zhuǎn)惡向善,國家才能得以治理。相反,如果不注重任人唯賢,即使費(fèi)盡心力于占卜、祭祀等儀式,人心卻不能轉(zhuǎn)變,也免不了敗亡。
關(guān)于任人尊賢的重要性,《群書治要·周易·益卦》中說:“自上下下,其道大光。”身處上位的人能以禮敬的態(tài)度對待在下位的人,前途一片光明。《群書治要·周易·屯卦》中說:“以貴下賤,大得民。”雖然身處高位,但能夠謙恭地尊敬地位卑微的人,一定能夠大得民心。
《說苑》中論述道:“人君之欲平治天下而垂榮名者,必尊賢而下士。夫明王之施德而下下,將懷遠(yuǎn)而致近也。”如果明智的君主能夠布施恩德,并且以謙恭的態(tài)度對待地位卑微的人,就能夠使遠(yuǎn)方的人得以安撫,使近處的人得以親附。
反之,“朝無賢人,猶鴻鵠之無羽翼,雖有千里之望,猶不能致其意之所欲至矣。”如果朝中沒有賢德之人,就像鴻鵠沒有翅膀一樣,雖然想翱翔千里,但最終也不能夠達(dá)到。“是故絕江海者,托于船;致遠(yuǎn)道者,托于乘;欲霸王者,托于賢。”如果想橫渡江海,就要依托于舟船;想行遠(yuǎn)路,就要依賴于馬車;想稱霸天下興起王業(yè),就必須依托賢德之人。
“非其人而欲有功,若夏至之日而欲夜之長也,射魚指天而欲發(fā)之當(dāng)也”。如果所任用的不是合宜的人,而想成就功業(yè),就如同是在夏至那一天,卻期望夜晚的時(shí)間長;向天射箭以求能射到魚一樣, 當(dāng)然是不可能的。這樣的事情對于虞舜、大禹這樣的人都是很困難的,更何況是一般的君主呢?
關(guān)于君主任人唯賢的效果,《袁子正書》中說:“夫處天下之大道而智不窮,興天下之大業(yè)而慮不竭,統(tǒng)齊群言之類而口不勞,兼聽古今之辨而志不倦者,其唯用賢乎?”想安處天下大道,而智慧無窮無盡;興辦天下的大業(yè),思慮不會枯竭;統(tǒng)一百家之言,而不費(fèi)口舌;兼聽古今言論,而心智不感疲倦,只有依靠任賢才能實(shí)現(xiàn)。可見,只有任賢使能,才可使君主不費(fèi)勞苦、自身安逸,就能使國家得以治理。
觀古宜鑒今,《群書治要》中所總結(jié)的君主用人的十重難處,也是當(dāng)今領(lǐng)導(dǎo)干部在識人用人中常存的問題、易犯的毛病。習(xí)近平總書記強(qiáng)調(diào):“用一賢人則群賢畢至,見賢思齊就蔚然成風(fēng)。選什么人就是風(fēng)向標(biāo),就有什么樣的干部作風(fēng),乃至就有什么樣的黨風(fēng)。各級黨委及組織部門要堅(jiān)持黨管干部原則,堅(jiān)持正確用人導(dǎo)向,堅(jiān)持德才兼?zhèn)洹⒁缘聻橄龋ψ龅竭x賢任能、用當(dāng)其時(shí),知人善任、人盡其才,把好干部及時(shí)發(fā)現(xiàn)出來、合理使用起來。”
《群書治要》中指出,用人直接關(guān)系著國家的興衰成敗、治亂安危。得賢首先要知賢,并把觀察賢士的方法總結(jié)為八觀六驗(yàn)、六戚四隱、三參、四慎、五儀、六驗(yàn)、七害、八征、九慮等等,以此全面觀察人的心性,判斷其是否賢德。觀人雖有方法可尋,但招納賢士最重要的因素還是“有德此有人”(《大學(xué)》),即修養(yǎng)自己,通過“同聲相應(yīng),同氣相求”(《周易》)的方式感召人才。得賢后,還必須敬賢、任賢。判定賢人應(yīng)遵循德才兼?zhèn)洹⒁缘聻橄鹊脑瓌t,重視選拔忠孝之士、賢德之士、廉正之士和讓賢之士擔(dān)任官職。任賢當(dāng)安賢,對待賢士要做到態(tài)度上誠敬、物質(zhì)上保障、制度上激勵(lì),這些都是感召和留住賢士的重要方法。而任賢尤其要注意避免求而不知、知而不用、用而不信、信而復(fù)疑,不能官非其任、祿非其功,杜絕求全責(zé)備、嫉賢妒能、聽信群小、黨派之爭等情況的發(fā)生, 因?yàn)檫@些都會導(dǎo)致失賢。
古人的用人制度體現(xiàn)了這些思想。例如,中國自漢代就實(shí)行了“舉孝廉”的人才選拔機(jī)制,要求官員的選拔必須秉持“爵非德不授,祿非功不予”的準(zhǔn)則,并進(jìn)而從官吏的選拔、考核、監(jiān)察、獎(jiǎng)勵(lì)、培訓(xùn)和管理制度上落實(shí)了“進(jìn)賢受上賞,蔽賢蒙顯戮”的主張,從而保證了德才兼?zhèn)涞娜吮贿x拔到領(lǐng)導(dǎo)職位上。在這種政治制度中,所有的制度建設(shè)都是圍繞著如何把人培養(yǎng)成為一個(gè)賢德之人、如何把賢德之人選拔在領(lǐng)導(dǎo)的位置上而設(shè)計(jì)的,其結(jié)果就是《六韜》中所說的:“不以私善害公法,賞賜不加于無功,刑罰不施于無罪,害民者有罪,進(jìn)賢者有賞,官無腐蠹之藏,國無流餓之民。”
習(xí)近平總書記在《領(lǐng)導(dǎo)干部要讀點(diǎn)歷史》的講話中談到,“中國歷史上凡是有作為的政治家都非常重視人才問題。他們深深懂得“為政之道,任人為先”的道理,在選人用人方面留下了很多可取的思想和經(jīng)驗(yàn),諸如知人善任、選賢任能,才兼文武、德才兼?zhèn)洌促t敬能、禮賢下士,訪求俊彥、唯賢是舉,人盡其才、才盡其用,避其所短、用其所長,勤于教養(yǎng)、百年樹人等等。”古人在長期政治實(shí)踐中所總結(jié)出來的系統(tǒng)的觀人、選人、得人、任人的思想、制度和方法,仍然值得今人認(rèn)真借鑒。
領(lǐng)導(dǎo)者閱讀《群書治要》,可以起到“古鏡今鑒”的作用,把提升領(lǐng)導(dǎo)干部的政治辨別力落在實(shí)處,這也是提升領(lǐng)導(dǎo)能力、執(zhí)政能力的重要方面。
* 劉余莉,中央黨校(國家行政學(xué)院)教授,博士生導(dǎo)師,中國傳統(tǒng)文化促進(jìn)會《群書治要》傳承委員會主任。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(xiàng)目“《群書治要》中的德福觀研究”(19BZX123)的階段性成果。